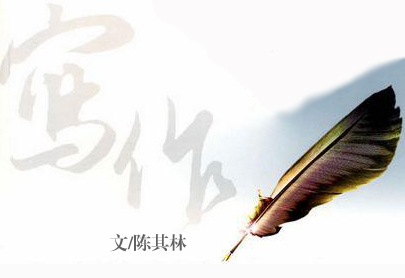
(一)
现在能写的人很多,而实际上把写作当做一个正儿八经的事业来做的人,有名有姓,冒出头来的人,并不多。
这个问题,在我看来,不是某个人的错,写的空间太大,都可以通过网络说一说自己的看法,读者不在乎多少,有就行,没有也没事,自恋一下。为此,才有了人人都是作家的感慨。
对于写作,我是认真的,主要源于我所接受的教育。
童少年时,我所接受的教育并不长久,总的算起来,只有七年。这也是我长期以来,有点回避,也难以启齿的话题。
记得十年前,我家乡中学七十年校庆,那所学校的一位老师,应该是校委会一的成员,亲手送给我一出席校庆的请帖,其意是,我“不小心”成为了家乡中学培养出来的作家。接上这请帖,我有点尴尬。为什么呢?因为我在家乡中学接受教育的时间,只有一年多,两年都不到。更不好意思的是,那个期末,我还得了个倒数第一。源于此,我离开了那所中学,早早地走进了社会。这个倒数第一,差点决定了一生的命运。
到我正式再一次拿起书本,是五六年之后,不是有意拿的,是无意之间。
应该说,我这类人,天生就是写作的。五六年之后,我就喜欢写几句,分成行,名为新诗,还养成了胡说八道,写日记的习惯。为了写好日记,为了把一首首的新诗写好一点,就翻起了字典词典,读起了书。记不清源于什么,突然自己下了狠劲,找来了中学与大学文科教材,两年不到的时间,被我全读了,还做了很多习题。也就在那一年,我在《写作》杂志上看到了武汉秘书速记进修学院的招生广告,我便报考了,是函数。通过大概两年多的时间,也考了那么几次,我获的了一张汉语言文学的专科文凭。随后又在名家推荐下,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了,去读了作家班,认识与接触了不少的名作家与文学同仁。
那时,虽在河北与东北的刊物上发了散文与诗歌,就是那样,写作也还都没有定格我的人生,不过,写作与读书,已经开始改变那个“倒数第一”将会降临给我的命运。
(二)
我一直以为,写作这个东西是要有点天赋的。人是需要表达的,这种需要,不仅需要说,还需要听。人也分很多种,就有这么一种人,眼睛睁的大点,情丰富一点,爱热烈一点。不过,这种人胆子都不大,在奔跑爱、情、事的道路上,缘于热一点,就会利用表达来武装自己,以狐假虎威的姿态,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害怕。或者说,用表达来为自己壮胆,有点像人喝酒。因此就构成了诗歌,构成了散文,构成了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部部小说。
历史的车轮走到目前这个时间段,对写作有天赋,并不是一件幸事。不过,对写作从文的人来说,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,第一,写作从文的人,是从善如流的人,从文是善良者的行为;第二,写作从文的人,离不开一个弱字,属于弱者的行为,从文是弱者在生活中抗争的武器。
近三十年了,我的生活中一直没能离开一个“写”字,而我童少年的经历,似乎决定了一生将会与“写”字与文化无关,对自己这种有点滑稽的变化,就多了一点思考。为此,我多次思考过自己童少年时期对写作有天赋的种种表现。
记忆中,最为清晰的,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语文老师是位名叫杨林的女性,那时才十七八岁的年纪,对我很严厉,也很友善。挨过她的鞭揍,关过我的禁闭,一起我扳过手腕,同我缝洗过衣服。一次作文,她拿出一两篇写得好的作文,当作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听。读完后,还多说了几句,提了一下我。说我在这次的作文中,写了一句很好的句子。文中是描写,有个晚上我去玩伴家里叫玩伴出来玩,因为是晚上,没有灯光。我在文中这样写道:我在黑夜中,叫了几声朋友的名字,回答我的是一片片的黑暗。杨老师认为这句子写的好,值得同学们学习。
现在回想起来,对杨林老师的敬业精神很是敬佩。
因为我在小学一年级开始,写字就不地道,老师的评语,均有“作业马虎”的字样,逐渐的,有了“马虎大王”的称号。直到很多年以后,去了北师大读书,山西一位学友,还送给了我一个外号,蝌蚪王。那时年轻的杨林先生能从我满是蝌蚪文的作业本上,扣到这么一句话,可以想象,当时她的那双眼睛,睁得有多大。
对于我认为自己对写作是有天赋的,甚至认为我天生就是写东西的,当我真正在记忆中去挖掘材料来证明的时候,这种材料又是极其有限的。小学五年级时的这个作文,杨林先生从我的蝌蚪文中找到的这句话,也就成为了我经常回味与自恋的一个场景。